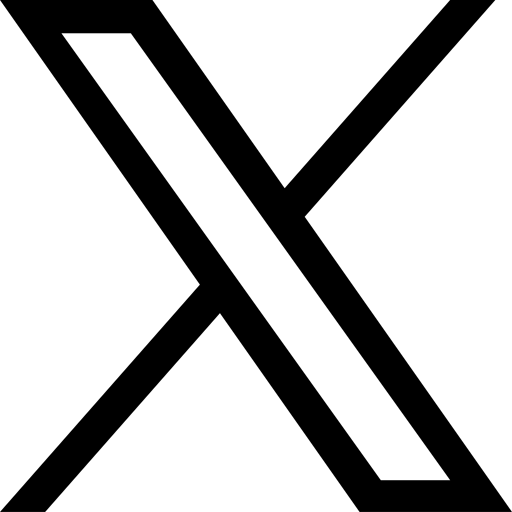29/07/2022Text: Helena Hau
在24小時都受到文化轟炸的年代,我們算是被文化氣息縈繞著?
「時代的轉折,在虛擬世界愈來愈重要的今天,人們並沒有絲毫放棄物質世界的跡象,人們仍然湧進城市。」這是茹國烈的新作《城市如何文化》的導論裏、無數尖銳的問題中,一句看似不起眼的平白直述。但簡易的描述中,卻輕輕道出了現今世代的三大課題——創新、傳統,以及如何在承載一切的城市中傳承與培育下去。
美國作家Lance Morrow說,「人們之所以旅行,是因為能從中學習到無法從其他地方學到的寶貴經驗。」茹國烈從事藝術行政多年,在2019年時,辭去了任職九年的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一職,帶著一個問題——「文化區建成後,城市就變得有文化嗎?」離開了香港。隨後,他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了一個關於城市的碩士課程,於此同時,到處遊歷,看看別人的城市是如何文化的。2020年底開始,茹國烈便以「城市如何文化」為題,進行了一連串的講座,至今合共50餘場。他將近年的學習、遊歷和交流的經驗逐漸整理成時次的新作,以「文化光譜BEAM」四個大方向——信念和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回憶、藝術和創造為出發點,闡述與分析這四點對於一座城市如何文化的看法。
文化離不開人的活動
在過去的週末,中環街市也有一場關於文化建築的講座,邀請了陳麗喬建築師、李亮聰建築師、林偉而建築師、張智強建築家,以及徐子晴博士與編者一同參與討論關於「文化建築」的話題。其中陳麗喬建築師提出了同一個問題——是否有文化建築後,城市就等同有文化了?關於這個問題,編者相信答案是否定。硬件的功能除了以性質為出發點外,其意義某程度也是人所賦予的,這裏就延伸一個問題——當這些硬件建成了,若沒有人的參與,它的存在不就是一個擺設?甚至是一個傷害?
2007年,世界知名演奏家Joshua Bell曾在華盛頓的一個地鐵內,用他那把價值350萬美金的小提琴演奏了Johann Sebastian Bach最複雜的作品之一,時長45分鐘,期間的路人只是匆匆走過,停下來的人也不多;然而就在幾天前,他在演奏廳內演奏了同一首曲,而當時的平均票價卻是100元美金,這個事件其實是Washington Post一個關於品味與價值觀的社會實驗,出發點為在一個日常的環境下,我們能夠認知藝術文化嗎?同時讓人沉思文化活動必須要在文化場所裏進行嗎?
文化的母體
嚴迅奇建築師在香港的兩個大型文化項目都逐步落成,包括今年開幕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正在進行的東九龍文化中心。從意義上來看,兩個硬件都屬於文化建築,但在語境上而言,故宮文化博物館無疑是承載著某種文化意義,但華夏文化必須在此才可宣揚嗎?並非,但它又何止為一個宣揚文化的一個硬件,它也是一種陳述。而當嚴迅奇談及東九龍文化中心時,他不禁地說了一句話:「我不希望這個工程會淪為大白象,所以我希望無論東九有沒有表演,大眾都歡迎及可以自由進出。」
當然,退一步來看,所坐落的地區與周邊配套設施自然也影響了這座建築的人流。故宮文化博物館坐落於西九文化區,雖然這裏有戲曲中心、M+、自由空間等文化建築,但這個十多年前才被劃分為文化區的新地區能否帶來一個強而有力的凝聚力,或許需要時間的見證;反觀東九龍文化中心,坐落於發展成熟的市區,周邊有完善的配套,在定位和設計上,走向更偏向於大眾化與通達性,讓文化藝術更加貼近生活,是伸手可觸的。
講座中,有人提出一個十分值得深思的問題——現時的文化建築就像一個monologue(獨白)多於一個dialogue(對話),這讓編者反思,為何人要到訪畫廊或博物館,他們想在那裡得到甚麼?到訪後,又會否重返?為甚麼要重返?
歷史是流動的,博物館是靜止的,當歷史走入硬件中,那麼它是流動的,還是靜止的?當我們說香港文化、香港藝術時,那麼是否先要弄清香港的文化母體?香港甚麼時候有文化?只有短短百年多的歷史,香港該以何種姿態站穩腳?它的特殊性又與其他城市輸入輸出文化時,有何不一?
有了文化建築,然後呢?
「倫敦之所以是個文化城市,在於它能讓文化種子在城市各個角落滋生出來。這些文化種子,扣緊了這城市不同社區中的信念和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和創造,以及記憶。」
除了上述的兩個大型文化建築外,早至60年前成型的大會堂、香港藝術館、尖沙咀文化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到JCCAC、饒宗頤文化館、PMQ、牛棚藝術公園、大館、H Queen’s、戲曲中心、M+、油街實現/油街二期等,不論是以文化建築為出發點的而建造的,還是活化舊有建築而成的,其實我們的城市從不缺文化建築,而且肌理也相當豐富,那麼回到問題本身,這些文化建築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是甚麼?若如茹國烈在書中所說,倫敦的文化種子能在城市各個角度滋生,那麼香港的文化種子要在各個角度滋生又缺少了甚麼養分?
【你點睇?】復活節現外遊潮,黃家和倡更好利用西九長期設立市集等吸引年輕人,你是否認同? ► 立即投票